云淡风轻,阳光灿烂,洒在海面上的光芒点缀了波浪,摇曳着,一片片金灿得耀眼。我独自走在细细软软的沙滩上,海浪顶着白色的浪头轻袭过来。这片沙滩,我和容子来过很多次。我走着,低头看见沙堆里有一枚光亮的玻璃。于是蹲下来,轻轻地拾起它,然后举起来,透过它去看头顶的蓝天。

“啊,好漂亮啊!”
耳畔响起容子的声音。“是啊,的确很漂亮。”
我说:“喂,你看,那朵云真有意思,就好像在天空飞翔的鸡蛋卷。喂……”没有声音回答我。
“喂……”
我回头叫容子。蓦然,身后还是那片寂寥的沙滩,还是那一次次涌上来的孤独的海浪,还是我一个人独自行走的足迹。低下头,我再次告诉自己:“原来,你已不在……”
没事的,有我
容子走了过来,停在了门口。夕阳照进房间,轻柔的风掀起窗帘。我转身看着她,容子也看着我,眼里闪动着泪光。我张开嘴,欲言又止。刚刚还在高声唱歌的她,终于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。
“你啊……”我苦笑了一下,打破了沉重的气氛,但是接下来却什么都说不出来,因为我也哽咽了。
我张开双臂,迎接着一头扑进我怀里的容子,紧紧地抱着她,“没事的没事的,有我在你身边,没事的。”
也许怀抱是我唯一能给她的一点安慰。但是我口口声声说着的“没事”却是那么软弱无力。什么叫“没事”,连我自己也不清楚,我还那样不停地说着自己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谎言。但是,那时那刻,我唯一能说出来的,也就只有这一句毫无意义的谎言了。
我轻轻地拍着容子抽搐着的背脊,让她在我怀里尽情地哭着。容子的泪水湿透了我的衬衫,渗到我的皮肤上,凉凉的。身为丈夫,面对哭泣的妻子,我的心里是前所未有的无奈和无能为力。,
我能做什么?我该做什么?我反复地问自己。我不能代替她生病,不能代替她痛苦,我能做的就只有这样给她一个紧紧的拥抱,给她一点点心灵上的依靠。在病魔面前,在生死面前,再伟大的人也只能俯首称臣。我渺小的力量又如何能撼动这个摧毁性的悲哀呢?我抱着容子,同时也抱着自己不知所措的心。
“没事的……”我继续机械地说着……
依旧是那最灿烂的阳光,它投射进来,用暖暖的光辉将我们这对无助的白发夫妻环绕在淡淡的金色中。从那一刻开始,容子一天天走向衰弱和死亡。她的生命就这样被突然宣判了,猝不及防……
回首,君已逝
看着挚爱的妻子即将离我而去,对我而言,这是一份难以承受的痛苦。我们一起走过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,穷日子的时候她没有怨言,也从不挑剔。容子是我的贤内助,生活中所有事情她都替我打点、为我准备,我从未担心过饮食起居。我们好不容易携手到白头,突然之间,永远的离别却摆在我们眼前。
面对生离死别,活着的人能做些什么呢?我该怎么做呢?守候在病床前,紧握着容子冰凉的手,我只能默默地祈祷,希望分别的时刻来得晚些,再晚些……
3个月过去了,容子并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离开,而是在病床上迎来了新的一年。不过容子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,一天不如一天,每况
容子不拒绝服用抗癌疫苗,我查到了一种疫苗的购买渠道,于是每周去一趟东京取药。独自坐在客车上,望着窗外的行人,我试着去想象每个人
我每天去两次医院,从家或者工作室走过去,路上买些吃的。我和容子每天一起吃晚饭,亲手把饭喂到她嘴里。我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着容子,吃完饭后就漫无边际地和她聊天。容子靠在窗台,我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,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,迎着温柔的光线,我们讲起很多往事:讲我们去旅游时发生的种种趣事;讲我专程去阿拉斯加待了一周也没看到极光的糗事……
身体状态好的时候,容子的笑声还是那么爽朗。容子性格开朗,喜欢和别人交流,聊天的同时会把自己的快乐传达给周围的人。不论走到哪里,只要容子是开心的,她周围的人也一定会跟着开心起来。护士小姐有时候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谈话中。她问我们一起旅游时会不会经常吵架,她跟她丈夫新婚旅行时,就开始吵了。
于是,容子解释了我们为何不吵架的原因:“到了观光地我们就各走各的,他喜欢逛名胜,我就是特别喜欢逛商店、买特产。所以我们想吵也没机会吵啊。”
说到极光的事情时,护士小姐都在笑我:“先生您居然不知道白夜现象啊!”我一脸尴尬,笑得最开心的却是躺在病床上的容子。
容子住院那段时间,女儿纪子几乎天天都在医院照顾容子,经常陪容子聊天。一天我还没走近病房就远远听到母女俩在笑。
一进门女儿朝我坏笑着说:“爸爸,原来是这样的啊?”
“什么这样的?”我不解。
“我长这么大一直以为爸爸和妈妈是相亲认识然后结婚的呢!”
“哈哈,你猜错了吧?”容子接过话去。
“我和你爸爸可是真正地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的。”
于是,我们又讲起在图书馆的相识,讲起那封坚决的绝交信,讲起我们奇迹般的重逢。
女儿嘲笑我:“看不出来啊,爸爸,你第一次见妈妈就上前搭讪啊?”
“哈哈,我那是真男人的行为,懂得该出手时就出手……”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我们都笑了起来,整个病房都被笑声点亮了。我们就这么回忆着过去的美好,谁都不愿去触碰即将到来的生离死别。
好景不长,进入二月,容子的身体越来越虚弱,
2000年2月24日,杉浦容子与世长辞,享年68岁。
我常常觉得,和容子的分别是那样的突然。检查出身患肝癌后的4个月,入院治疗后的两个多月,容子就永远地离开了。太突然,我甚至没有准备好该如何去面对。作为比容子年长4岁的丈夫,我从未想过容子会走在我前面。容子曾经答应过我,一定照顾我直到我离开人世的那一天,因为没有她我就不知道该怎样生活。
“我知道啦,你走了以后我还要健健康康地活十几年呢!”容子的声音仿佛还在耳畔。而如今她失约了,先走了,留下不知所措的我。
容子走了,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,但是每次意识到她已经不在的时候,我都会觉得不可思议。家里每个角落都有她的身影。她在我面前打扫着,在我耳边说着话,一切都还那么清晰,仿佛就是上一秒钟的事情。可下一秒她却不在了,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容子走了7年了,可我依然没能适应没有她的日子。写关于她的故事时,我总会在不经意间叫她:“喂,容子,你还记得我们去那个地方旅游时你为了买便当没赶上火车吗?喂,喂……”
抬头一看空荡荡的房子,客厅、厨房……到处都是空的,只有我的回音。这时,我才反应过来,不得不再提醒自己,“啊,原来你已经不在了……”
当我低头继续写作,过一会儿又会不自觉地叫:“喂,容子啊……帮我加点茶好吗……”
最后的日子
容子最后的那段日子,每天都要与病魔抗争,每天都要忍着疼痛接受治疗。因此那些日子就像一张张排列着的灰白卡片,但最后留下的画面却是一张耀眼的彩色明信片。
那一次,在纽约工作的儿子回来看望母亲。因为隔得太远,儿子担心一旦母亲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也不能及时赶回来,所以他专门请了假,捧着一大束鲜花,回来看望母亲。当儿子收拾行李准备起身,我打算把他送上出租车,于是也跟着起身了。
容子的目光跟随着我们,正要出门的时候,身后传来容子的声音,爽朗高亢的声音:“有一!”
我们回头,突然容子从床上支起身体,要下床,滑了一下,好不容易站稳。更让我吃惊的是,下一个瞬间,容子整理整理病服,朝着儿子微笑着挺直腰敬了一个军礼,说:“一路顺风!”
瞬间,世界安静了,我们都怔住了。
容子那么精神抖擞地站着,背后是透过窗帘的暖暖阳光,她站在那里,闪着光芒。
看着母亲的笑靥,儿子也随即举起手来朝着母亲回敬一个军礼,“是!我出发了!”
空气凝固了一会儿,看着互相敬礼的母子俩,我哈哈地笑了起来,容子和儿子也都笑了。我们脸上都笑得那么开心,但是眼中却含着泪水,我们心里都知道,这是母亲跟儿子最后的道别。
身为小说家的我,见过也写过很多场面,但是容子最后一刻的爽朗是我没见过也写不出来的。我们都被她“欺骗”了,她明明心里无限悲伤,脸上却还绽放着灿烂的笑容。
后来儿子说,长时间的旅途中,他反反复复想起好几遍母亲最后的姿势和笑脸,忍着盈眶的眼泪,儿子一遍遍地举起右手行军礼,“是!我出发了……”
每次回忆起那一幕,我都说不出话来。不,是颤抖着泣不成声地默念:“这样一个最后的谢幕方式,对于给了我这么多年快乐的你来说,再合适不过了……”
格兰米勒的音乐再次响起,我恍惚回到了那个与容子重逢的夜晚。吊灯旋转着,洒下点点金黄色的光芒,酒色氤氲,音乐弥漫,我牵起容子的手走向舞池。
容子一袭白裙,配一双精致的白色高跟儿鞋。偌大的舞池只有我们两人,没有天花板,抬头便是皎洁的月亮。我们轻轻地迈着舞步,听得见彼此的呼吸。
“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容子低着头对我说。
“但是我一直相信我们还能再遇见。”
“呵呵,你真会哄女孩子,这么会说话。”容子以为我是在讨她欢心。
“不,我是说真的。”我肯定地说,语气坚定。容子停下了舞步,抬起头,怔怔地看着我。
看着容子清澈的眼睛我告诉她:“你知道吗,这是命中注定的。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,一切都注定好了。”
容子笑了,“你怎么知道呢?”,
“因为你是我的守护天使。”
“守护天使?”
“你将一生守护我,让我幸福快乐。我们此生要彼此相依在一起,这是命中注定的。”
四目相对,容子看到了我的一颗真挚的心,她迎过来轻轻地抱着我,音乐继续,我们的舞步继续。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就是我们一生的约定。

美国密苏里州有一名可爱的5岁男孩叫巴特菲尔德,他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是戈西奇,可不幸的是,戈西奇患有血癌。巴特菲尔德决定与他同甘共苦,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支持好友。 ...

清朝雍正年间,台湾古城新竹,有个名叫戚务生的书生,要去福建参加福州3年一度的秋季乡试科考。那时台湾是隶属福建省的府级行政区。 书生戚务生搭乘一艘木制大商船,从旧...

话

可怕仇怨 铁勇的母亲一愣,勉强朝我笑道:“小哥,有什么事吗?” 我快速走到门边,将那铁钩从桶里面拿了出来。 播放一个恐怖的鬼故事 铁勇的母亲脸色大变,目光变得惊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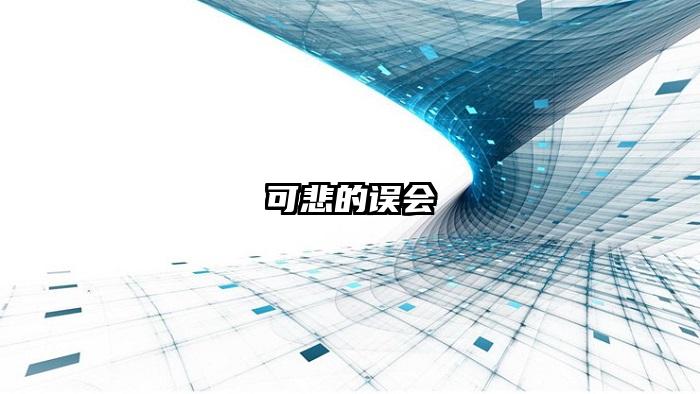
早年 恐怖鬼故事 原创 在美国阿拉斯加地方,有一对年青人结婚,婚后生育,他的太太因难产而死,遗下一个孩子。他忙于生活,又忙 小男孩说恐怖鬼故事 于看家,没有人帮...

冲突珉敬迅速走进电梯,看到19层的按钮亮着,一个男子扣着帽子,无法看清脸部,站在电梯里面。珉敬透过镜子偷看男子的模样:旧帽子,突出膝盖的休闲裤,完全不搭配的大衣...

咎由自取 得弄清楚那伙人让两位老人干什么事,最好是根据这条线索找到那伙人。 “千斗,你刚才说你要证实什么,是咋回事,现在能证实了吗?”村长望着我。 我点点头,基...

城北郊有个大鱼塘,塘主是五十多岁的牛三爷。 这天下午,牛三爷正在塘边撒鱼食,一辆乌黑贼亮的轿车下了公路,沿着机耕道开到塘边,从车上下来个三十多岁的汉子,径直走到...

沂河岸边有个叫柳树屯的村子,村北有一片叫北洼的沙土地,土质肥沃,水源充沛,极适宜种植西瓜。可多少年来,村民们只在这里种植粮食作物,从没有种西瓜的。原因是与北洼相...

大家都知道,人们对居住环境非常讲究。尤其有钱人家在建宅之前,都要请风水先生过目。然后根据阳宅三要先定其大门方位,再确定主屋、厨房位置。小户人家看不起风水,只好根...

女人来到大师的地下室。大师吃了一惊,那颗蓬乱的人头差点从托着的两手间掉落下来。 大师把头颅正了正,怒问:你是怎么进来的? 女人看到大师的头颅与脖颈处的涔涔血迹,...

第二天,一如往常的上课,但外面的天色似乎让人显得很难受,万里无云,但是太阳却显得惨白惨白的,一点都不刺眼,反而让人有种冰冷的感觉,傍晚的时候,凌家村的七大姑八大...

不知道你们自己真正遇到鬼是个什么感觉?至少我那个时候是肯定吓慌了的,虽然那鬼并没有什么恶意。 我家是开豆腐坊的,而每片豆腐上面都要用可食用的颜料盖上我们这个坊的...

高老头年逾60,手中钱多了,晚 恐怖片 世界上最恐怖的短片鬼故事 张震鬼故事 年的生活自然过得称心如意。但自古贫贱自在,富贵多忧,高老头尽管晚年幸福,可还有一桩...

珍妃怎么被打入冷宫的呢?众说纷

眼看要过年了,黑子的女人也要回来了。女人下广东快一年,黑子在家盼得心里生疼,早早就给女人留下了好吃的,那是三块糍粑,他和儿子舍不得吃,小心地将糍粑放在大海碗里,...

争执 林小渊提前放了暑假,就到H城找自己的高中同学郑涛玩。本来约好,郑涛会到火 恐怖短篇鬼故事百度 车站接他,但当他下了火车,却接到了郑涛的电话。对方抱歉地说临...

楔 子 三条人影爬上了香山别墅的围墙,然后悄悄地跳了下来,他们的动作都很迅速,很灵活,显然是经常干这种翻墙入院的勾当。 事实上,他们三个正是每个城市都会有的以偷...

夜里12点多,任珊珊听到敲门声,她有些诧异地走到门后问了声:谁呀? 外面没有声音,倒是手机响了起来。号码是一个任珊珊认识的快递员,接通后,快递员说:有你的快件,...

来次艳遇 许新山坐在旅馆的软床上,心里没着没落的,出差前妻子那句出门在外别动花花肠子的话,扯动了他那根敏感的神经。要真次艳遇 玩泥讲鬼故事恐怖医院 ,远在千里外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