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的"窝囊"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他不善言辞,老实巴交,胆小怕事,遇到困难就爱流泪。小时候,我是个非常顽劣的孩子,天天逃学,从没有一天静下心来学习。
每到年终,父亲总是抄着手站在家门口,眼巴巴地望着邻家的孩子捧回一张张三好学生的奖状,而我总是低着头,两手空空地回家。为此,父亲很是失望。上四年级的时候,有一次年终考试,我的数学考了个"大鸭蛋",语文也不及格。
班主任老师害怕我拖了班里的后腿,劝我留级;而学校勒令我不用去上学了,让家人前来办理转学手续。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,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他顿时惊呆了。继而,便蹲在地上"吧嗒、吧嗒"地抽起了旱烟。
第二天,父亲提着一篮子鸡蛋领着我来到了校长家里,任凭父亲磨破嘴唇,可校长还是坚持让我转学:"这孩子学习太差,跟不上。"校长有点不耐烦了,劝我们回去。
这时,令我终生为父亲感到屈辱的一幕出现了:父亲突然"扑通"一声跪下,流着泪说:"校长,您就看在我这张老脸的分上,将我这娃留下吧!如果下学期他拿不到三好学生奖状您再开除他行吗?"
父亲这一"壮举",虽然使我免遭到转学的厄运,但那时的我却认为父亲给家人丢尽了脸。父亲下跪的事很快就像长了翅膀,传遍整个校园,我成了人们嘲笑的"跪读生",那一段时间我发了疯似地学习。但年少的我不感激父亲,认为父亲是个"窝囊"透顶的人。
第二年,当我把平生获得的第一个三好学生的奖状交给父亲时,他竟像喝醉了酒似的,在那两间简陋的、巴掌大的小草房里转来转去,对母亲不停地唠叨着:"贴在哪里好呢?"最后,父亲决定贴在他炕头的墙上。
父亲用图钉摁好后,反复摸着我的头问:"山子,什么日子你的奖状能把这面墙贴满呢?"
以后的岁月里,我每年都能带回几张"三好学生"、"优秀团员"之类的奖状,父亲总会庄重地把它们一一贴好,并且时间顺序井井有条。土墙上的奖状,成了那两间穷得连一张年画都没有的小草房里唯一的一道风景。
每逢家里来了客人,父亲总是把人领到那面土墙前"参观",并摇头晃脑地拖着长腔给人家念上几张。有时还拿到村上去,向人家炫耀。看到父亲的这些"表演",我心里感到滑稽可笑。
高一那年,我在全县语文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,当我无意中将奖状交给父亲时,一向不善言辞的父亲竟像着了魔一样疯疯癫癫地跑到街上,到处吹牛:"我儿子考了全县第一名,将来绝对能考上大学。"
"别吹牛了,难道你忘了为儿子下跪的事?"有人趁机揭父亲的疮疤。"我儿子有这个奖状为证,你儿子有吗?"父亲不服气,举起奖状和人家吵起来。
想不到一生谨慎、胆小怕事的父亲,这次竟和人家动起武来。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外人打架。最后结果可想而知,老实的父亲被人家打得肋骨折了几根,最后住进了医院。

事后,我不但不同情父亲,反而认为父亲是自作自受。
待父亲出院回到家后,我压在心头多年的火终于爆发出来,冲着父亲大声吼道:"爹,你往后不要再这样丢人现眼了行不行?这些破奖状有什么好炫耀的?你被人家打成这样,还不都怪你吹牛惹的祸!"
父亲低着头一声不吭,那表情像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。我越说越气,随手从墙上撕下几张奖状,边数落父亲边撕得粉碎。这时,我发现父亲的眼里蓄满了泪水……
第二天,令我惊异的事情发生了,我发现昨天被我撕碎的奖状又被人一点点地粘了起来,重新又被人贴在原来的位置上。母亲告诉我说:"你别跟爹过不去了,他窝囊了一辈子,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为了这几张撕碎的奖状,你爹流着泪整整拼了一个晚上。"
听了母亲的话后,我心想,父亲"窝囊"了大半生,没得过什么荣誉,大概是借儿女的奖状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吧!
数年后,我成全了父亲的愿望,考上了大学,父亲收集奖状的劲头也就更足了。待我参加工作后,那面黑乎乎的土墙已被父亲用花花绿绿的奖状和证书贴满了。每当看到这面土墙,我就想,这些年来,父亲辛辛苦苦地摆弄这些奖状到底是为了什么?我甚至怀疑父亲是不是有点心理变态。
但真正使我认识父亲的,却是家里发生的那一场火灾。
据母亲讲,那场火灾是因为邻家的孩子玩火,不小心点着了自家的房子,我家的房子也跟着遭了殃。当时,父亲刚从田里回来,二话不说,扔下锄头,便闯入了那两间烈焰腾腾、浓烟滚滚的小草房里。母亲和周围的邻居都惊呆了,都在想,窝囊了大半辈子的父亲哪来这么勇敢、果断,难道这几间破屋里藏着比他生命还重要的宝贝不成?大约过了八九分钟,父亲满身是火,摇摇晃晃地跑了出来,一双胳膊紧紧地护着胸口,好像怀里揣着一件稀世珍宝似的。
就在父亲跑出来没几步,忽然身后"轰隆"一声闷响,那两间草房惨然倒下,父亲也忽然昏厥过去……待母亲和周围的邻居把父亲抬到安全的地方,父亲已不省人事,唯有额头上那凸起的血管恰似一条条蠕动的蚯蚓。
当母亲小心翼翼地挪开父亲那双瘦骨嶙峋的胳膊时,发现父亲怀里揣着的竟是一摞发黄的奖状--那是我从小学到今天获得的全部荣誉。
我永远忘不了在医院见到的情景。父亲昔日那浓浓的眉毛,稀疏的头发,乱蓬蓬的胡子全烧焦了,身上也被烧伤了多处,原来的肺病更重了,不停地咳嗽。他睁开那双苍老、无力的眼睛,慈爱地注视着我,用微弱但坚强的声音告诉我:"孩子,你的那些奖状一张也没烧着,待我们房子盖好后再重新贴上……"
我的眼泪"吧嗒、吧嗒"地掉了下来。那一刻,我终于明白,儿子本身就是父亲的作品,儿子的每一点成绩,每一分进步,都是贴在父亲心头的奖状,儿子的成功就是父亲终生渴望、梦寐以求的莫大荣誉。
这时我才明白,父亲原本并不"窝囊",为了儿女的前途,那父爱何计生死荣辱呀!

午后明媚的阳光照在白色的沙滩上,远处的海岸边,一个孩子欢快的尖叫声传进了我的耳朵。一个父亲和他年幼的儿子正在小沙丘上相互追逐。父亲追上了自己的儿子,将他高高举起...

父亲一生对钱守得很紧,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用,可一辈子下来,父亲没存下多少钱,反而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,很早就得了高血压。母亲一生对钱看得很淡,时常穷大方。母亲...

父亲是个哑巴,这一直是我心中一块隐隐的痛。我的家在一个偏僻的小镇,父亲就在小镇的拐角支了一个烧饼摊赚钱养活全家。听人说,我的老家并不在这儿,是父母后来搬到这儿的...

我是9岁的时候跟着母亲带着弟弟来到这个家的:三间土屋、一个小院,他是这个家惟一的主人,老实而憨厚。当我们娘儿仨站在他面前的时候,他搓着大手,呆立在原地不知所措。...

读中学时我开始叛逆,总嫌大人们不理解自己。 父亲送我14岁生日的礼物,是一本《简·爱》,因为父亲觉得我肯定会喜欢这样的故事。是的,我确实喜欢,却恨他不了解我早已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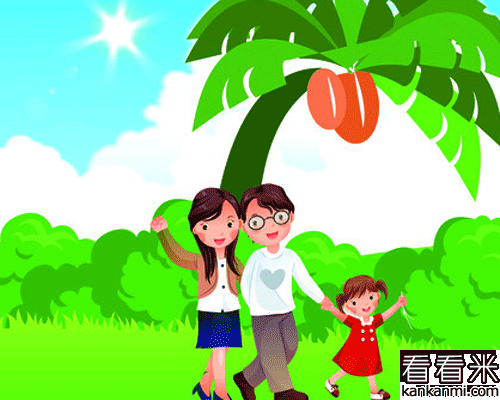
毕业后留在了离家千里之外的北方,虽然春天有大风,虽然夏天太短,但冬天却有我喜欢的暖气,让我的冬天不再寒冷。安定之后,几次三番打电话回家,让父母过来小住,他们都推...

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来娱乐中心应聘,要求做专业按摩师。我问他:“您有按摩经验吗?”他摇头表示从零开始。我又问他:“您要求薪水是多少?”他说不要薪水,就是想来学习。...

读完朱自清的《背影》,我想起了我的父亲。 现在已是一个月未见父亲了,着实有点想他。虽然平常没少通电话,但总觉得见到他的人才会安心。 父亲今年整整59岁了,头上的...

一天,弟弟在郊游时脚被尖利的石头割破,到医院包扎后,几个同学送他回家。 在家附近的巷口,弟弟碰见了爸爸。于是他一边跷起扎了绷带的脚给爸爸看,一边哭丧着脸诉苦,满...

父亲比我大了整整50岁,老来得子,高兴得放了两大挂鞭炮,摆了10桌宴席,还开了那瓶存放了两年都没舍得喝的五粮液。 8岁时,父亲带我去学二胡,从家到少年宫,骑自行...

对于一位父亲来说,一生中最幸福也是最难过的时刻,莫过于在女儿的婚礼上,挽着她的手走过红毯,然后,像割掉心头肉一样,把她交到别人手上。看着她头也不回地走向明亮确定...

一、怪事这个月的月初开始,宏远超市发生了一件怪事,每周五的小食品百货区,都会丢失一包奥利奥饼干。刚开始,超市经理大魏以为是员工登记出了错误,因为接着奥利奥饼干摆...

凛冽的寒风中,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正在一栋大楼的阴暗处摆弄着垃圾,看样子他似乎毫不嫌弃,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塞能吃的东西。 众人都看不下去了,对他说:“孩子,那是垃...

1.从来没有温柔地对待过他第一次听到“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”这句话,我读高一,一天晚自习的时候,从前排一个娇滴滴的女生口中蹦出来,带着一点儿小矫情、小炫耀。就...

小时候,父亲对我的要求很严格,让我倍感压力。因此,我在心里对父亲产生了不满和抵触的情绪,觉得父亲太冷酷了。 有一次,父亲正在院子里磨米粉。那时候,乡下没有加工粮...

我有一味药,那便是父亲的爱。多年来,我像一个病人一样,依赖这味药。磕磕绊绊的人生,不大如意的人生,在每一次受到挫折和打击,每一次感受到彻骨疼痛时,我能够得以迅速...

爸爸拉着我的手,看着火向我们把头的房间烧过来,说了短短的一句话,影响了我的一生:“孩子,不怕,有爸爸在,一切都是身外之物。”我的爸爸张藜是个文艺工作者,然而因为...

一18岁那年,我高考落榜决定去深圳打工,可母亲死活不让我去,非让我再去复读一年。母亲在我耳边絮絮叨叨个不停,我没好气地冲了她一句:“我考大学,谁供我读?谁来管这...

一我和他一直都没有共同语言。我总怀疑自己是他捡来的,但事实上,我的确是他亲生的儿子:有与他一样棱角分明的脸,一样淡漠冰冷的神情,甚至眉毛的走势,都是一样的倔强而...

爸,人家都说:女儿是父亲的前世情人,从前世追到今生来延续未了的情缘。可你总是笑着对我说:上辈子我是你的债主,今生来向你讨债的。是啊,22年来,是你为我和妈妈撑起...